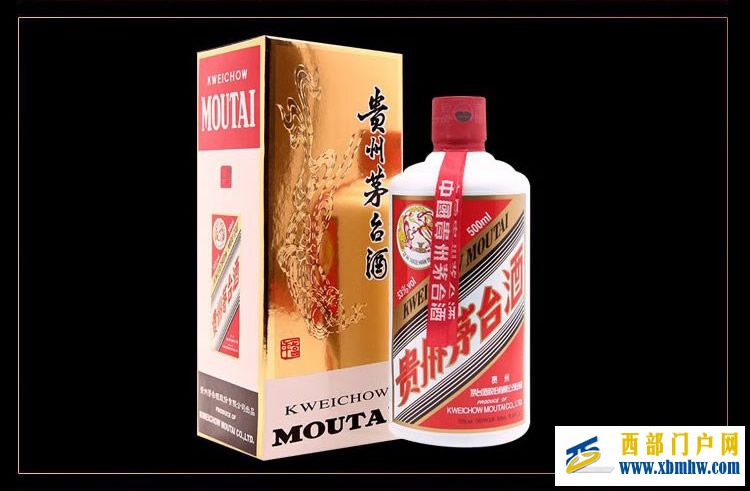AI復活親人引爭議 是療愈傷痛還是傷口撒鹽?

于浩在訓練自己的數字人
本報記者 李一能
那一天,在親朋好友面前,大屏幕上的妻子用不太標準的川普,笑著感謝大家來為她送行。她安慰大家不必太過悲傷,最后還特別叮囑女兒,好好學習,有可能的話,希望她也能學醫,繼承自己未竟的理想。
那一刻,看著被AI“復活”的妻子,張元(化名)不知不覺淚流滿面。
今年清明節來臨之際,“AI復活親人”業務在網上熱度飆升。對這一新生事物,人們看法不一。有人認為有助療愈失親之痛、彌補未竟之憾;也有人覺得這是“在傷口上撒鹽”,存在倫理與法律上的爭議。
但在殯葬業人士眼中,“復活親人”遠非AI技術運用的終點,背后還藏著一個更為雄心勃勃的計劃——數字“永生”。今后,也許每個人都可以提前備份自己的人生,在數字世界實現生命數據的永恒留存。
一
“復活”親人
打開購物網站,輸入“復活親人”,會跳出許多鏈接。只需一張逝去親人的正面照片,花5元錢就能讓人“動起來”,會眨眼、會微笑;花50元能讓照片“開口說話”;花90元還能配上逝者原聲。這項業務的搜索熱度近期暴增600%。
“今天就有幾十個人來咨詢,生意太好,忙不過來。”“網絡復生師”張偉(化名)認為,近期“復活親人”的火爆,是熱門事件與科技成熟推動的雙重結果。
不久前,音樂人包小柏利用AI技術“復活”逝去的愛女包容,引發巨大關注,很多人因此了解到AI技術“復生逝者”的應用。
“有些人覺得有點怪,認為不符合傳統觀念,但也有很多人好奇,加上馬上就是清明節,所以想嘗試一下。”張偉說,他的客戶對產品效果大多比較滿意,其中不少人都是剛剛失去親人,數字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思親之痛。
另一個原因,是近年AI技術高速發展,數字人制作成本大幅降低,曾經幾千元甚至上萬元才能做到的事,如今不到百元就能完成。這也讓張偉這樣的“網絡復生師”成為一種新職業。
盡管如此,張偉對這一行的未來并不看好。“門檻太低了,軟件操作其實很簡單,競爭太激烈。”而且,通過基礎軟件“復生”的數字人,效果并不十分理想,人物表情僵硬,聲音聽上去沒有感情,離“栩栩如生”還有一定距離。新鮮感過去后,有沒有回頭客要打一個問號。
“除此之外,這一行還有不少風險。主要是隱私和倫理,處理不好會遇到很大問題。”張偉認為,客戶傳來的照片涉及個人隱私,如何使用需要商家自律。但目前商家無法確定客戶是否有照片使用權,以及生成數字人的用途。張偉擔心如果這一技術被濫用,或有違道德倫理,或涉嫌違法犯罪,協助制作的商家也要承擔相應責任。
二
特殊告別
張元至今還記得,妻子臨終前消瘦的樣子,眼神中滿是不舍,看著他默默流淚,卻已說不出話來。
作為醫生,妻子曾經治愈過許多病人,卻沒能救下自己。不到40歲就成為醫院的骨干,妻子的敬業與醫德有口皆碑,哪怕生命即將結束,她也決心要以醫生的方式離開——捐獻遺體,讓三位病人因她獲得新生。
感佩于這位英年早逝的女醫生崇高品格和感人事跡,為她操辦葬禮的福壽園提出,想為她制作一個紀念視頻,在追思會上播放。其中有一個環節,是制作一個數字人,讓她“親口”向親朋好友們告別,并留下最后囑托。
對此,張元一開始是拒絕的。他一直無法接受妻子離開,怕看到妻子的數字人受到二次打擊。念初中的女兒卻勸說父親,她想永遠記得媽媽的樣子,讓大家知道媽媽是一個特別了不起的人。“如果媽媽知道,她一定會支持。”
最終,張元被女兒說服了,提供了制作視頻的資料和數據,包括妻子的照片、視頻、語音信息等。對妻子最后的心愿與囑托,他也盡量配合工作人員回憶。完成信息采集后,他忙著操辦追思會,沒特別在意這件事。直到那一天——
“看著視頻中那熟悉的微表情和習慣動作,我突然覺得老婆就在眼前,她真的又回來了。”張元說,瞬間的心痛后,他感到心中那塊被堵住的地方突然松動了,所有的情緒與悲傷得到釋放,流下的淚水中更多的是感動。張先生確信,女兒的選擇是正確的,這場告別彌補了不少遺憾,妻子的精神和期盼得以留存,會成為家庭的寶貴財富,不斷傳承下去。
“在那一刻,技術其實是次要的,核心是找到了可以觸及人心最柔軟一面的情感。”籌劃這場葬禮的福壽云總經理湯旸認為,數字人技術在殯葬業的運用,不是為了炫技與煽情,而是幫助逝者家屬更好地生活,讓本無感情屬性的人工智能,成為承載溫情的容器。
三
數字殯葬
今年清明前夕,上海各大墓園大力推進節地生態葬,其中,包括運用AI技術的“數字葬”。2018年,福壽園上線數字化殯葬平臺“福壽云”,今年推出了數字家祠、數字禮葬、數字禮祭、數字人模型等數字化服務。
“一個現實的問題是,實體墓地越來越稀缺,保存的逝者生命信息也很有限,因此AI技術、云技術、元宇宙一定是殯葬行業未來發展的方向。”福壽園國際集團副總裁范軍認為,“復活親人”近期備受關注,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殯葬行業十多年前的探索與思考。
“要弄清這件事的本質,要從人類殯葬行為的本源去理解。”范軍認為,殯葬的核心目的,是留存信息,遺體代表著生物信息,而墓碑、墓志銘則蘊含著逝者的生命信息。“每個人都會死兩次,第一次是失去生命,第二次是被人遺忘。”動畫電影《尋夢環游記》中的這一觀點,范軍非常認可,以現在的科學技術,讓人生命永存并不現實,但讓人的生命信息被永恒保存,已經可以做到。而AI數字人技術在殯葬行業運用的終極目標,就是將逝者從形象到聲音,再到記憶性格,甚至思維模式進行全方位的保留。“人類文明傳續的模式,都可能因此而改變,未來人們也許可以實現與先人對話交流,他們的經驗與思想,將以更為直觀的方式呈現。”
范軍表示,AI技術、云技術等在殯葬領域的應用研究,近年已越來越多被運用到線下業務。“比如,吳孟超院士、著名媒體人曹景行的葬禮,都使用了數字人技術。傳統墓地物理屬性占80%,精神屬性占20%,隨著科技進步,這兩個數據會發生逆轉,今后殯葬業發展的方向,一定會更加注重精神傳承。”
四
備份人生
科幻電影《流浪地球2》中,人類通過“數字生命計劃”將意識轉化為數據,實現在數字世界的永生。轉移意識,在現階段來看還太過玄幻,但依然有人探索另一種可行性——“備份人生”。
杭州拱墅區云家族科技有限公司前臺,立著一臺一人高的全息倉,一個數字人“看見”有人來訪,主動打招呼:“您好,請問有什么可以幫您?”
這位“前臺”,就是這家公司CEO于浩的數字分身。通過AI訓練,數字分身不僅在形象和聲音上與“本尊”極為相似,更是保存了一部分他的記憶、思維模式甚至是口頭禪,能夠與人簡單交流。
“本質上,它是我的一個備份,就像是孫悟空吹猴毛變出來的分身,可以幫我做各種事情。”于浩認為,外表、聲音的復制如今很容易實現,難點在于保存記憶、思維模式、表達習慣、性格特征等,這是人們區分彼此的各種要素。
于浩和同事們將這些要素分為六個維度的模塊,通過多個AI大模型分工協作模擬人的思維,并錄入大量個人信息對AI進行訓練。理論上,訓練越充分,數字人和真人的相似度就越高,直到真假難辨的程度。
哪些人用得到數字分身?不久前,一位客戶找到于浩,為了讓父母排解寂寞,要求訂購一個孫子的數字人陪爺爺奶奶聊天;還有一位客戶,父親被查出重病,可能只有不到兩年的壽命,最近又開始健忘,于是希望“緊急搶救”父親的形象與記憶,盡可能為家人多留下一些信息。
“目前使用比較多的場景,是心理創傷療愈,如果數字人使用得當,確實能幫助逝者家屬盡快從悲痛中走出來。”于浩說,制作殯葬場景的數字人時,他們會參考心理創傷療愈師的建議,讓數字人開導家屬,幫助他們盡快接受現實,而不是沉溺其中無法自拔。“這就對一家公司是否堅持科技向善,提出了很高的要求,也需要政府部門嚴格監管,防止技術被濫用。”
今年清明,數字人概念火爆,公司也在上個月剛剛實現盈利。也許這波熱度不會持續很久,但于浩對“備份人生”的前景充滿信心。每天工作之余,于浩都會抽空完善自己的“人生手賬”,記錄每天發生的事情,以及想讓他人了解的信息,這些都將成為訓練于浩數字分身的關鍵信息。“百年之后,我會離開這個世界,但我的數字人會永遠存在,后人可以和它聊天,從而了解我是一個多么有趣的人。”
五
制度建設
今年全國兩會上,人工智能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。一個重要議題是如何加強制度建設,為這一新興產業健康發展保駕護航。數字人作為AI技術率先落地的重要使用場景,在法律與倫理上存在的爭議,引起專家學者高度關注。
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部合伙人劉春泉律師,曾擔任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。“將數字人技術運用于緬懷逝者、安撫人心無可厚非,但前提是本人與家屬授權。”劉春泉認為,如果有人擅自將逝者信息制作成數字人,甚至以此牟利,就可能觸犯法律涉嫌侵權,即便逝者已經不享有民事主體的權利,其家屬也可以依法維權。
這一新生事物帶來的另一潛在風險,是存在公民信息被盜用的可能。劉春泉認為,任何視頻、照片、語音都可能被用來制作數字人,如果被用于電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,危害不容忽視。“雖然現在的技術還不能完全以假亂真,但說不定哪天就能實現突破,要未雨綢繆。”
劉春泉認為,對于規范AI數字人等新技術的使用,司法界早有研究討論。“一方面要提醒公眾注意個人數據信息隱私的保護;另一方面也要呼吁法律及時跟進,在問題出現之初,就完善相關規定,為技術發展提供制度保障。作為企業,也要前瞻性制定并遵循一定的技術協議,保證數字人可追溯可識別,具體實現路徑,要由技術專家與法律專家共同討論。”
這也是業內不少專家的共識。上海長三角智慧城區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沈建平認為,制作數字人,特別是“復活”逝者的行為要謹慎。“用得好可以傳承思想、撫慰人心,用不好就是傷口撒鹽,帶來糾紛與困擾。”沈建平指出,不久前有人擅自“復活”去世的明星,用于平臺引流,給家屬帶來了傷害。
“一個成功的案例,是不久前上海永福園中國人民志愿軍紀念館,在獲得家屬授權后,利用數字人技術讓一位71年前犧牲的烈士用鄉音念出一封家書,社會反響非常好。”沈建平認為,AI和殯葬服務行業包括生命教育等,核心的結合點還是在文化傳承上。“以這樣的初心去進行‘人工智能+文化’的創新,可能會催生一種新的文化業態。”